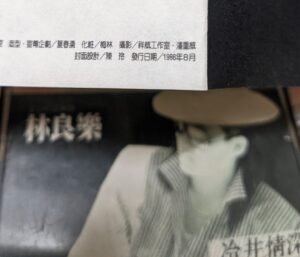潘重威Photo /

自千禧年後,我們不曾再見過王傑,中間輾轉從媒體知道他的訊息,證實我感覺他在香港的不快樂。
在台灣的我們,同時也被科技與數位化的發展徹底地改變了,千禧年後的唱片公司只能一再縮編,屬於90年代最黃金的唱片年代正式告終了。
很多優秀的唱片人被迫裁員,要不轉行,留在娛樂業的無不自尋出路,生存逼著我們汲汲向前,工作和現實抓住了我們當下的關注,要不是因為2020年的新冠肺炎大爆發,讓全世界的人們放慢了生活的腳步,要不是疫情,潘先生應該沒有餘裕的時間,回頭整理自己。
他原只是想練習斷捨離,沒想到整理出更多他早已離掉,卻根深蒂固的曾經,這個曾經,是他拍攝唱片封面的職涯青春,竟然二十幾年過去了,而王傑,正是這個曾經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在潘先生整理出過去的傳統底片,只有王傑是有留下黑白印樣的,因此可以在數十卷的底片中,先挑出幾張試著簡單清潔復原後,送去爵士掃成小圖檔,再次看見1995年的王傑佇立在溫哥華街頭,不得不說潘先生是最能捕捉王傑浪子氣息的攝影師。
接下來發生的事,根本有如奇蹟一般,這些舊照引來絡繹不絕的傑迷,他們的愛意深厚到超乎我的想像,且是來自世界各地,聽他們說更多王傑的點點滴滴,比曾與他共事的人都深刻,我們也因此重新認識了王傑。
此時此刻,才是認識王傑的第四個階段
一則臉書的PO文,自動引來五萬人的瀏覽,沒有任何廣告,完全是傑迷的自動自發,發文的當晚,回應就像吃角子老虎和中了柏青哥般噹噹噹地湧進來,王傑不是隱退了嗎?這些歌迷對王傑的每一張專輯、每一段專訪如數家珍,我們還因此得知,潘先生釋出在溫哥華拍王傑牧場的那匹駿馬,後來竟然死了。
因為王傑怕天冷,在馬房四周放好暖爐想讓馬兒取暖,反而造成馬兒熱衰竭死亡,因此還被加拿大政府開重罰,天啊,這真的很像王傑耶,他是個心中充滿愛,卻不太懂得如何愛的人,我始終這麼覺得。(怕是有傑迷又要罵我了>//<)
我這麼說王傑,其實很冒險,因為我沒想到曾經在周刊專欄寫過王傑,字字都還被傑迷如數家珍,王傑果真就像我在1987年第一次聽到他,他的存在本身就像魔咒,依舊深刻地盤旋在他的歌迷腦裡,這魔力的穿透,沒有任何一個新世代歌手做得到,因為它的背後有更深層的理由。
王傑的年代,人人都可以自我定義
再也沒有一個世代能像90年代,那是國語流行音樂的黃金高峰,也是台灣剛自報禁解除後生長的新沃土,出版業有如雨後春筍,有聲出版更成為年輕人追求文化的大宗,從王傑「一場遊戲一場夢」到張雨生「我的未來不是夢」,勇敢追夢,是那個世代的共同語言。
這些夢想,在深夜中陪過學子讀書,在失戀時陪著傷心落淚,為不被了解的孤獨中幫著放聲嘶喊,也在與死黨發瘋的每一首歡樂K歌中,陪伴很多人走過成長懵懂,不敢說王傑代表90年代,但他卻是把90年代精神活出最精采的其中一個。
從學生運動的民歌時期後,王傑代表正式面向社會大眾最底層的心聲,他的歌,更是引領藍領向上的一股能量,人人可以昂首闊步,當時的我們,甚至可以偉大到讓三級貧戶成為民選總統,還有甚麼夢,是90年代辦不到的?!
然而,偉大的千禧年也是改變的分水嶺,變好變壞,我們無從置喙,一切都發生得太快,快到我們都需要時間才能回頭看,這些經歷都代表了甚麼,可以確認的是,那個高峰令人驕傲的90年代過去了,它被雪藏在每個人的記憶角落,再也沒有時間想起。
第一次,我們感謝有這場疫情
與其終日惶惶不安瘟疫何時過去,不如把時間拿來整理自己、整理過去,從雜沓的心抽絲剝繭自己失去了甚麼、還擁有甚麼,才發現這些底片的寶藏依在,雖然經歷歲月的摧殘,但他們屹立地發出幽微的光,甚至因為經歷了時間,更顯珍貴。
修復底片其實是個大工程,現在的每一張照片都是經過專業藥劑的清潔,再到沖印公司掃成小圖檔,還沒有經過正式電修的原圖。
潘先生並不滿意目前修復的質量,卻被傑迷流傳得很廣,甚至被推上的微博王傑超話的精華帖,還有人自製影片和運用照片自製紀念品。(殘念啊,誰叫網路無遠弗屆,天下不守規矩的人大有人在)
我多希望讓大家見到,潘先生腦裡想呈現的王傑影像,那一定會是攝影的超級傑作,好希望傑迷不要急,等著修復好的照片跟大家好好見面,於是想辦場攝影展的念頭,隱隱約約浮現。
但要展出王傑的照片,就非得得到他的本人同意不可,我們開始嘗試聯絡傑哥,但他在加拿大的住家電話早已經更換,都已經二十幾年過去,大多的工作友人與之失聯,我們只好在他的個人微博留言,幾乎毫無音訊。
最後幸運地,在飛碟的老同事打聽到他的聯絡方式,他人在加拿大第一時間回覆了潘先生,我們順利地拿到王傑簽好的肖像授權同意書,同時得知華納將為王傑發行「這場遊戲那場夢的結束篇」專輯。
即便他人在加拿大,至今沒回台宣傳,專輯還是上了唱片銷售排行榜和電台點歌榜的榜首,我想,王傑會不會結束,這不是他一個人說得算,我想這是肯定的答案。
(未完待續)
相關文章:王傑一場遊戲夢結束了嗎?